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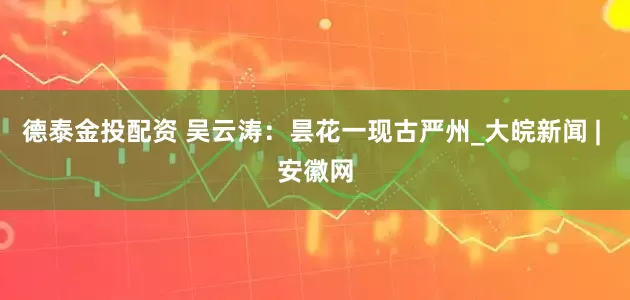
唐朝武德年间,为削弱隋朝旧制影响,废除郡级建制,推行州县二级制,全国大量增设州县,州数达300余个。安徽境内设立的古严州就是这一政策的产物。
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安徽严州诞生在皖西南宿松县境内的严恭山下。这里北枕大别山余脉苍莽的脊梁,南临万里长江浩荡的波涛,控扼吴楚咽喉,古驿道穿境而过,为江淮防线要冲,地理位置险要非凡。在唐朝军队与辅公祏等江淮残余势力激烈角逐的烽烟里,严州以其特殊的区位,成为舒州总管府(治所在怀宁)支撑前线、转运粮秣、拱卫后方的一道无形堤坝,默默承载着唐朝这个新生王朝稳定东南的重任。
安徽宿松的严州仅存在于唐武德四年至七年(621~624年),存续不足三年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宿松,武德四年以县置严州……有严恭山。”“严”字借自山名。作为临时军事管制区,严州仅辖宿松县(后增辖望江县)。其职能限于唐初安抚江淮的权宜之计,并未形成稳定的行政体系。
宿松严州的记载除了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地理志片段,主要见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及明清《安庆府志》《宿松县志》。史书对“置废严州”仅寥寥数语,均未嵌入宏观的历史叙事。宿松严州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逐渐湮没、沉寂。
宿松严州虽是昙花一现,其意义却远超其短暂的存在本身。
首先,它是唐初在江淮大地上一次重要的行政实验。武德年间,全国州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旋即又因“地狭民稀”或“务从省并”而大量裁撤。宿松严州由置到废,正是这场规模浩大的地方治理探索与效率优化的鲜活缩影。它如同一块试金石,检验着新政权的控制力与行政成本间的微妙平衡。其次,宿松严州这片土地的血脉里,早就沉淀着远比唐朝更古老深厚的人文基因。早在东汉,这里就是松滋侯国的所在地。严州的设立,仿佛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道桥梁,无形中接续了这片土地独特地缘身份与文化薪火。
与宿松严州的沉寂、淡化不同,历史上还另有一个同样名为“严州”的千年古州。它在浙江的钱塘江畔,其命运轨迹与安徽的“严州”判若云泥。浙江严州(睦州),自唐武周时肇基,直至民国初年才废府,存续千载有余。地理位置上,它扼守三江汇流之要冲,是徽商巨贾扬帆入杭的必经门户。地方人文方面,它因范仲淹的德政、陆游的诗篇、朱熹的讲学,以及方腊起义的烽烟、太平天国的血战等等,而深深镌刻进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。一部部《严州图经》,一卷卷《严州文献辑存》,乃至今天的“宋韵严州”的文旅盛景,都在通过持续的事件叠加、文化深耕与学术传承,把一个古地名淬炼成为放射光芒的地域符号。
反观宿松的严州,却没有这样的幸运。其实,在宿松严州的山水间,并不缺少浓墨重彩的精美华章。严恭山庄严灵秀,山间古佛千年,曾流传禅宗五祖弘忍驻锡的传说,石壁镌刻着“南无佛顶首楞严”的佛偈,“严恭石道”亦仙亦佛,玉屏峰铭记着明代史可法“四顾云天倚玉屏”的绝唱,云天岭回荡着烽火抗日的悲歌。明末史可法、张献忠血战丰家店惨烈悲壮,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于此血战……无数慷慨悲歌、铁血烽烟,无不以“严恭山”或“玉屏峰”“淳风堡”之名载入方志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此地华严寺编纂《文选》,首任县令张何丹在此留下仙田瑞谷的美谈。
然而,严州废后,宿松复归舒州,历史的光辉更多地凝聚在一座座山名、古寨,以及县乡的名号之下,“严州”二字,彻底沉入水底,化作一声幽叹。这些璀璨的文化碎片,如同散落的明珠,从未串联进“古严州”的叙事之中。松滋侯国的青铜遗韵、仙田瑞谷的文脉、严恭山的佛踪、古寨群的烽烟,始终处于零散状态。
悠悠千载,山河无言。我们需要的,或许是站在这片浸透铁血与禅思的土地上,以历史的视野,去缝合那些散落的光阴碎片——将松滋侯国的古韵、唐代严州的建制尝试,熔铸于皖西南吴楚雄关的独特叙事之中。唐时州城在这里虽仅存三年,但在文化记忆中,也能穿透迷雾,获得新生。
嘉喜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